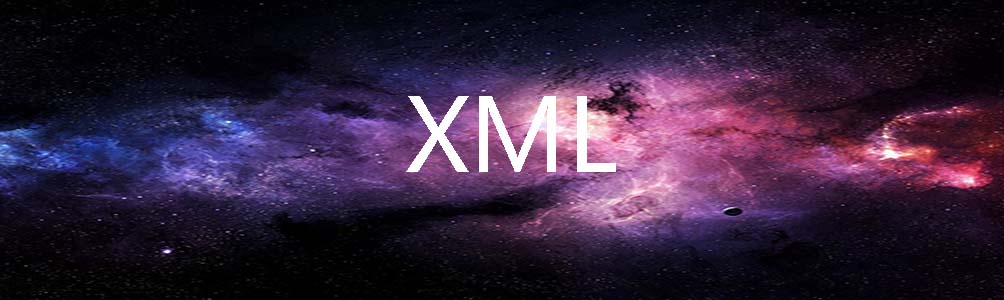王琦三角刻刀下的忠贞和睿智
▲王琦
虽已到北京60多年,王炜说家里说的一直都是重庆话,父亲王琦更是对重庆充满着特殊的感情。
父亲生前,当得知以自己命名的博物馆坐落于重庆的中心——中山四路,并与周公馆、戴笠公馆相邻之时,非常感动。“他觉得太奇妙了,那条古老的文化街,他年轻的时候经常在这条马路上穿行,没想到在自己近百年的时候又回到那里。这也是他始终所认为的,要回到重庆这个地方。”近几年一直陪伴父亲左右的王炜,感受得到父亲的内心。自小受到父亲的影响也从事版画艺术,王炜多年来也持续进行版画历史研究,相对于古元的温和、彦涵的奔放、李桦的严谨、力群的质朴、黄新波的含蓄,他认为父亲的最大特点则是睿智。
王琦总被称作版画界的元老之一,他是中国新兴木刻版画老人中的最后一位。可是版画并非是他艺术生涯中的全部,他还为中国美术理论研究和美术史专业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中国美术馆藏王琦版画作品展
年,老人将件作品捐赠给中国美术馆;十年之后,他又将剩余的作品和文献全部捐赠给重庆。年底,老人以望百之年辞世,为自己的艺术和人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年有两场关于老人的重要展览: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中国美术馆藏王琦版画作品展2月23日开展;5月,重庆王琦美术博物馆也将举办王琦大型回顾展。一场在重庆,一场在北京,冥冥中的巧合,让后辈再认识这位前辈所经历的从新兴木刻到当代版画的一生步履。
艺术梦想与革命,怎么选?
“儿时的记忆总是朦胧的,而雾蒙蒙的重庆更加给我留下了朦胧的记忆。山城重庆笼罩在一股潮湿的雾气之中,嘉陵江两岸高高低低的吊脚楼鳞次栉比,万瓦云集;江中船舶往来不绝,远处时时传来低沉而忧郁的汽笛长鸣;对岸江北的景色在晨雾中时隐时现……”这是王炜对重庆的记忆,而这记忆也大多来自父亲的写生作品。
他与父亲,就像是一个世纪里不同时代的两位行者,总是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感受,相信他对重庆的最早印象也是父亲对重庆的最早印象。不同的是,王炜出生时正值战乱年代,而父亲则出生在还算太平的民国时期一个殷实的贵族家庭。
成长在一个因循施教的家庭,自家的私塾里,王琦从小就是幸运的。16岁考入上海美专,第一次离开重庆。
“当我第一次跨进上海美专的大门,最吸引我眼球的就是陈列室挂着的那十几幅欧洲绘画名作。虽然是刘海粟校长临摹的,但同样深深地震撼着我!我在这些作品前,反复驻足欣赏,不舍离去,特别是米勒的《拾穗》和德拉克洛瓦的《但丁的小舟》,使我感到绘画原来如此的广阔!表现力如此的丰富!站在这些作品面前,我才感到艺术的天地原来有如此之大!真是太震撼了!”这是王琦在《世纪刻痕》一书中与王炜对话时回忆的往事,从这时起,王琦的心理就埋下了去法国追逐更为广阔艺术的种子。
▲中国美术馆“典藏活化”系列展:中国美术馆藏王琦版画作品展
一位年轻人,站在时代的十字路口上,他热爱艺术,也参加了革命。艺术与革命,之于年轻的王琦,都无法割舍,却在必要时必须做出选择。在上海美专毕业那年,王琦20岁。“他想去法国学油画,他跟我说那是他20岁时的梦想。但是抗战爆发了,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就毅然选择投入了抗张的洪流。他说抗战将自己的美梦打破,从此中国少了一个油画家,却多了一个版画家。”王炜对雅昌艺术网说。
在上海读书时,除了想去法国学油画,王琦也对木刻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年前,九旬过半的王琦还清晰的记得自己是如何近乎狂热的喜欢上版画:“在读书期间,上海给我印象最深的画展有‘张充仁水彩画展’‘第一回全国木刻作品流动展’‘全国漫画展’和‘第一届苏联版画展’。其中‘苏联办画展’我先后去看了三次,这个展览对我后来走上木刻版画创作道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毕业之后的王琦经美专时的老师倪贻德介绍,进入武汉三厅。当时的武汉三厅聚集了大批文化人,当时郭沫若任厅长,田汉则任三厅艺术处处长,那天,田汉接待了包括王琦在内的一群年轻人,还包括王式廓、周令钊、冯法祀、力群、罗工柳、李可染等。当时的武汉三厅艺术处相当于现在的中国文联,美术科相当于现代的美协,三厅这批文化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成为文艺界各级领导。这群年轻人,就这样被一起卷入了抗战的洪流中。
▲王琦的版画处女作《在冰天雪地中的游击队》年12×9.4cm中国美术馆藏
回到重庆
年,王琦前往延安鲁艺学习木刻。四个月的学习期很快就结束了,他的同学们都希望他留在延安,而当时王琦则受到了冯法祀的影响,坚持要回到大后方——重庆。当然,回到重庆,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对重庆有着特殊的情感。
临别延安的前一天晚上,他与上海美专的同学杨角,睡在窑洞的土炕上畅谈一宿。“杨角说,如果你一定要走就走吧,回去之后一定要做到两点:第一,创办一本美术刊物,开辟后方的美术阵地;第二,解决组织问题。”王炜回忆父亲的故事。王琦就这样风风火火的投入到了抗战美术的道路上。第二年,《战斗美术》创刊,杂志的编辑部就在重庆机房街号,王琦家的亭子间,一个7平方米的地方。创办者还包括王朝闻、冯法祀等,赞助人则包括周恩来、郭沫若、茅盾、艾青、田汉等。
年是王琦生命中重要的一个年份,是他回到重庆坚持革命的开始。王炜说:“为什么说他对重庆情有独钟?从工作层面来说,抗战期间他在重庆领导了当时的中国木刻研究会,一直主持着工作会的工作。一直主编《战斗美术》。所以从年开始,他投身到革命美术事业中,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早期的黑白木刻版画尺幅特别小
版画艺术家代大权这样介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版画现状:“新兴木刻运动在上海沦陷、国势危急之际,兵分两路,一路远赴西北的延安,成就了边区版画,探索着版画与民众相依的路径;一路便是在王琦先生的直接参与和领导下,在大后方的重庆继续着版画与时代互动的努力。”
所以我们现在再来看抗战时期的版画,古元、力群等边区版画家表现的题材更多的是农村新面貌、新生活;重庆是国统区,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则不同于延安,王琦带领的版画家们更多表现的是劳苦大众、现实的黑暗等。王炜研究版画历史多年,谈到这一现象时,他说:“两个区域的版画发展就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其实是统一的。当时延安跟重庆版画界联络非常密切,而且这些来往都由周恩来的秘书负责传递,周恩来的周公馆就是重庆版画界人士经常聚集的地方。他的秘书张颖经常把延安的木刻带到重庆,将重庆的木刻带到延安,可见共产党在当时对版画界的支持,版画在当时已经作为一种武器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王琦《当警报解除之后》版画11.5x10cm年中国美术馆收藏
▲王琦版画嘉陵江上年13.3×16.6cm中国美术馆藏
▲王琦版画《当难民车停下来的时候》年9.5×12.6cm中国美术馆藏
还是年,王琦刻出了他的版画处女作《活跃于冰天雪地中的我游击队》,发表于《新华日报》,这是他真正动手刻木刻的第一张作品。一方面需要创办杂志,另一方面生活的重压压得王琦喘不过气来,但他挚爱的木刻创作却一刻也未曾停止过。回忆那一时期的创作,王琦很喜欢《马车站》,他觉得黑白处理和刀法运用都相对比较成熟了,题材是从自家大门前马路上停留的一辆马车得来。“我在刻《马车站》时,常常把原版放在衣橱顶上,再三揣摩,看看自己刻好的部分有什么不妥之处,同时考虑下一步如何动刀。我一面抱着你,一面抬头看着木刻原版,身体还摇摇晃晃地作自得其乐状。”王琦曾经对王炜这样回忆,当时的木刻版画的确存在很多问题,包括技法的问题、艺术性的问题等,整个版画界不断的探讨,当然这样的讨论也包括版画艺术应该是自由的还是应该为政治服务这样的话题。
王炜介绍,在技法层面,父亲的版画创作也在不断的变化,艺术手法不再是纯粹的黑白色块和阴阳脸,越来越明快的画面开始出现,更善于用线条,陆续接受了苏联、德国、英国版画的影响之后,才逐渐摸索出一条中国的路子。
重庆之于王琦重要,最终还要回归于他的生活——在重庆找到了自己终身的伴侣。老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在聚会上风趣的跟子女谈及自己的感情:“在上海美专的时候,女同学是不少的,临别时的留言簿中,女同学写的文字也是很生动的,也有女同学想追我,可是我觉得那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当我回到重庆,一看到你妈,就知道就是她了。纯清的少女型。”
“父亲是将婚姻与爱情结合得最完美的典范。他一生始终如一地深爱着我们的母亲,而母亲始终如一地爱着我们的父亲。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他们相依为命、同舟共济,迎来了幸福的晚年生活。”王炜介绍,在父亲最后的日子里,写下了他的肺腑之言:“我一生算得上是幸福美满的一生。首先有一个相爱的生活伴侣,还有一个温馨和睦的家庭……”
重庆是他的家乡,是他最早工作的地方,也是他生活的地方,又是他找到终身伴侣的地方,所以即使在那个年代他肩负着家庭的重担,生活所迫要不断的奔波,可是他依然觉得那是他最喜欢的城市。
▲50年代王琦的套色版画
▲王琦版画《天堑变通途》年41.8×80cm中国美术馆藏
艺术上的高产
抗战结束之后,由于新兴木刻运动的工作需要。王琦带着全家人离开重庆,辗转南京、上海、香港、广州,走南闯北。他的身份也由单纯的版画家开始转变,因为在重庆期间从事编辑、教员工作,尤其到上海之后,从事艺术教育的工作越来越多。50年代初,王琦最终落脚于中央美术学院,他在版画家、教育家的角色上又增加了一个身份——理论家。
“在中央美术学院28年的教学生涯中,有25年是副教授。从教学上看,我父亲从一开始就是身兼两个系的工作:版画系和美术史系。他始终不放弃两支笔,一支史论写文章的笔,一支版画刻版的笔。”王炜感慨,尤其当下被提及较多的就是父亲参与了央美美术史系的创立,如今著名的理论家、美协艺术理论艺委会主任薛永年分别在60年代考中央美术学院史论系,以及在70年代考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的时候,主考官皆是王琦。
▲王琦版画《晚归》年16×24.2cm中国美术馆藏
▲王琦版画《长白山的早晨》年65.2×45.5cm中国美术馆藏
▲王琦版画《青年炼钢工》年35×45.5cm中国美术馆藏
后辈都认为,王琦版画的创作高峰期其实是上世纪70、80年代,而那一段时期也正是他最为忙碌的一个阶段。主持了中央美术学院两个系科的工作、担任了《美术》杂志的主编,70岁了还临危受命,主持中国美术家协会的工作,无论是艺术、工作还是社会活动,他总能独当一面,直到80多岁才退休。
培养起了美术史研究的一批新人,也带领起了版画界新的中坚力量,在真正退休之前,老爷子还全盘考虑了美术界的未来,最后确定了由刘大为接任美协的领导工作。所以,王琦成为老一代艺术家最后一位殿后的领导者,为他这一代的人的工作进行了完美的收尾。
相对于工作,王琦说这一时期“我才刚刚踏进版画艺术的大门”。或许是几十年的积累终于迸发,老人在最忙碌的这一时期,却创作出了比以往更为成熟、更多的版画,其中不乏他的经典代表作。从早期的黑白版画,到50年代的套色版画,再到这一时期的成熟版画,王琦对于版画的控制开始呈现出炉火纯青的状态,从以往的简单画面转向更为繁杂的内容呈现,他开始用版画表达工业题材、都市生活。
▲王琦版画《林海巡逻》年60.5×45.2cm中国美术馆藏
▲王琦版画《古墙老藤》年27.5×40.3cm中国美术馆藏
▲王琦版画《古榕道上》年27×40.4cm中国美术馆藏
▲王琦版画《夜曲》年30.3×45.2cm中国美术馆藏
“从版画人的角度来看,父亲的版画创作最可贵之处就在于画面没有一丝杂音。就像他对灰调子细腻的刻划,灰色中千变万化,拓印的过程中一不小心就会糊版,印好了黑白灰三种调子就会非常明快。他的很多作品都有无数层次,画面表现了无数内容,表达起来却一件一件来龙去脉清晰可见,层次分明,尤其是与树木题材相关的绘画,层层山林、树木,没有多余的一刀。”王炜感慨。
在王琦一生的作品中,最爱描绘和刻画树木,在他的画册中,甚至有小一半作品都是以树木为描绘对象。“不论农家小院的杂树,还是黄瓦红墙的古柏;也不论是春夏参天华盖的茂叶,还是秋冬萧索瘦劲的枝条,他都以锐利而敏捷的三角刻刀,尽展那些树冠繁叶的茂密、枝桠交错的挺拔。那些他刻刀下的树木,其实就是他生命不断向上伸展的象征,也是他俊俏挺拔、风骨伟岸的人格寓意。那幅《古墙老藤》岂不就是他自己的精神肖像吗?老干虬曲,却枝叶丰茂;藤蔓苍劲,却风姿绰约。这何尝又不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株历尽岁月风霜的常青树。”《美术》杂志主编尚辉这样评价。
为何父亲会如此钟情于树木?同样也喜欢树木题材版画,与父亲同行74年的王炜能感同身受:“为什么要刻树?因为刻刀在木头上碰撞出来的力度是任何艺术形式都无法替代的,这种树皮的质感只有用刀才能表达出来,别的艺术形式是无法达到的。”
诗人艾青曾经为王炜的一张《棕榈》写过一首诗,或许能解读出王琦对于树木的刻划:没有比他更坚硬,笔直直地站着,像一个个哨兵,满身是铁骨钢筋,连叶子也像刀剑,指着苍茫的上空,我每次看见它,赞叹它树皮的构造,像是盔甲的鳞片,用刀也无法砍断,现在由你用木刻刀,表达了他的忠贞,我多么感激你!
创作出大量经典作品之后,90年代初的王琦在版画创作上戛然而止,因为视网膜脱落而做了手术,从而结束了他的木刻生涯,睿智的老人并没有痛苦和纠结,从此封刀。放下刻刀,拿起了毛笔,转向水墨画的创作,用版画家的视角去表现他所感兴趣的山水,从此踏上了他水墨画的新旅程,直到95岁高龄。
▲王琦版画朝霞映船台年55×40.5cm中国美术馆藏
▲王琦版画都市交响曲年46×35cm中国美术馆藏
后记:
父亲身患重病后,王琦便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在他最后的日子里,我亲身感受到他面对病魔病痛的那种淡定、自信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强烈地感受到他对一生追求的坚守和永不放弃的初心。”王炜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这样表达。
正因为老人的这种坚守和初心,以及永远从容和豁达的生活态度,才让他在历次社会运动中安然的度过。王炜还回忆了这样一段故事:“在年,美院进行‘肃反’运动中,父亲被当作一个重点对象进行审查,那时我才13岁。公安人员到我们家搜查,那天夜里倾盆大雨,一直搜查到半夜。可是我父亲还是对我们说,这是为了保卫全中国人民的安全和利益,欢迎公安人员来家中搜查,你们的爸爸不是坏人。他们把父亲所有的笔记本、文献都用两个大麻袋抄走了。审查后,结论是没有问题,事后父亲却一如既往的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高强度的工作和艺术创作几十年,在后辈看来源于王琦超强的记忆力和永不知疲倦的精力。尤其是老先生的记忆力不同凡人,即医院的时候,老先生的记忆力依然没有丧失。王炜对雅昌艺术网说,父亲退休之后向媒体敞开心扉,不断接受采访,对于半个世纪前的故事、人、地点、时间都表达清晰,就像刚刚发生过,对于采访都能对答如流,坐在旁边倾听的王炜每次都获益匪浅。“老爷子80多岁时,在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他就让能把邓小平在文代会上发言的两大段话一字不差的背诵下来,现场速记整理出来之后真是一字不差,很多学生辈都傻眼了。”美术界都一致认为,这个老头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的百科全书,是活化石。
回到文章开始,年在重庆与北京,纪念这位刚刚故去的艺术界前辈,不仅是对王琦先生本人艺术的崇仰,他代表了这一代人,这也正是对这一代艺术家所作出卓越贡献的深情回眸。
作者:刘倩
编辑:张丽敏
放心收藏,全球见证,扫码立即送鉴
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