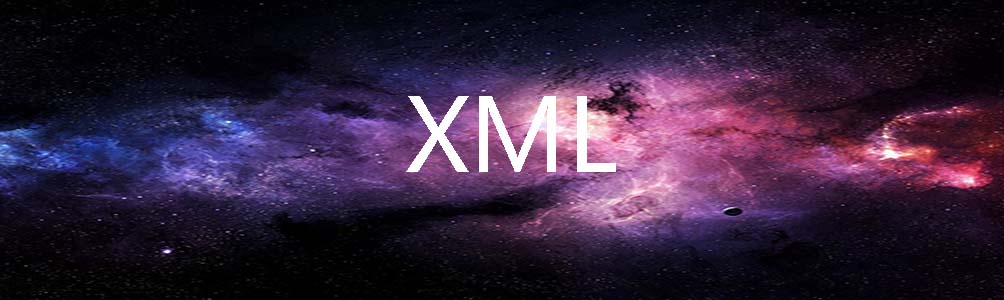成都中医药大学宋兴教授伤寒方的运用
成都中医药大学宋兴教授《伤寒方的运用》(
后世主张伤寒方运用应当灵活化裁的专家,对这个问题都有非常深刻的体会,他们响亮提出:有是证用是药。中医强调的证不是症状,症状只是证的外在形象表达,证是疾病表里寒热虚实的本质属性,包含着疾病发生发展转归的核心机制。所以,辨证加减是经方运用的基本原则。令人遗憾的是,在国内中医队伍里,能辨证化裁运用经方的医生是少数,对症状进行治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医生反倒是多数,国外的情况我不太清楚,想必也好不到哪里去。说得难听一点,只能对症状的,就不是合格的中医,甚至可以说对中医还没有入门。因为同一个症状,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多种病症都可以见到的,比如痛,无论是头痛还是脚痛,寒热虚实都可以引起,简单运用止痛方药怎么可能收到好的疗效呢?临床上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十多年前,一年轻女性痛经患者就是个比较典型例子。患者16岁,12岁初潮就痛经,越来越严重。每次行经都小腹痛、头痛,还伴有肢冷、呕吐,甚至昏厥。四处求医,找不少中西医专家都看过,西医镇痛为主,中医以疏肝行气止痛为主,效果都不明显。我接诊时,见到的临床症状是:舌苔黄腻,脉滑数有力,小便热,一派湿热阻滞的特点。这个病,临床所见大多是虚寒性的,用温补温通方药的机会较多。这一例却是湿热性的,是个比较特殊的例外。当时有一位山西的学员在跟我临床学习,帮我写处方,我告诉他三仁汤加银花连翘,他半天都不愿意写,他认为是我搞错了。他说,疼痛那么严重,老师还用银花连翘清热药,那不是会导致气血更加凝滞,下次痛起来更厉害吗?学生讲的也有道理,但不是联系实际的道理,而是脱离实际的从众死理。我让他重新体会脉象,观察舌象。我说:湿热特点这么典型的舌脉,如果都不能辨,不敢认,那中医诊断就没有价值可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患者服用后,疼痛立止,效果非常好。我们的老祖宗早在明清时期,就已明确指出:湿热邪气交织在一起时,清除湿热是一个漫长过程,所以我建议患者连续吃药到下次经行。但年轻人不愿意坚持服药,只服用半月后,脉缓和,舌苔变干净,小便也不热了,就不愿再服药了。这个女孩很幸运,第二个月,痛经没有发生。但我仍坚持告诉她:治疗并没有结束,后面三五个月内,如果有吃药的毅力,每次月经来之前的一周,吃几剂药,并且饮食要清淡一些,这对巩固疗效可能有重大意义。患者配合还算良好,此后疼痛很少发作,即便偶有发作,也症状轻微,而且辨证用药,立见功效。反观这个病例的治疗方药,没有一味止痛药。所以我再三强调,无论援用何时何人的方,在自己的临床运用中都必须加减化裁!必须辨证运用!绝不是机械照搬!绝不是对症状用药!用心研读一下《伤寒论》就可以知道,作者本人就在加减。在书中,与桂枝汤相关的条文有50多条,所派生的方其实也是桂枝汤的加减方,明确谈桂枝汤加减的还有20多条,这就是最好的范例。再认真学习一下《伤寒论》序言,作者在序言里表达出的学术传承观点是什么?是强烈反对各承家技,始终顺旧这种保守的门户风气他怎么会不允许后人对自己作品中的方进行加减呢?朋友们,同学们:对于《伤寒论》中医方的运用,无论什么名家大腕告诉你说不能加减,你听听就可以了,不用去理会。这只能说明他自身虽然顶着名家的光环,但他对《伤寒论》的理解,就一直存在有重大偏差,而且始终不能觉悟。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工作的灵魂,是法宝,但辨证论治理念的养成,却是有一定难度的,难就难在四诊资料的指向,很多时候并不一致。不是热证就一定脉洪大有力,舌红口渴,便秘尿热等热证证据充分展现,很多时候是不充分的,甚至有可能是背离的。比如有些热毒内盛的大热证,反而脉沉伏不见,舌黯便溏,乍看一派虚寒现象,这恰恰是邪热内盛,气机壅闭的表现,不仔细辨认,就很容易误诊误治。当然,这属于火极似水的特殊矛盾,临床并不多见。就是普通病症,也未必四诊指向一致,明明是寒饮潴留的五苓散证,却常见口干口渴;明明是阳虚内陷的补中益气汤证,却常常脘腹、四肢发热,甚至全身发热,个别特殊病例还热象典型。五苓散证的渴,未必舌燥唇裂,未必真能喝水。补中益气汤证的热,未必脉三部都强劲有力,未必二便闭塞,这些都是鉴别要点,考的是医生的诊断水平。辨证论治原则的掌握有难度,但是一旦掌握之后,又是最为提纲挈领,执简驭繁的。一个中医师,如果辨证论治成为他临床诊治的常态,那是最轻松不过的,同时又是应变能力最强的。因为无论何种病症,只要演变为同一证,那就是同一种治疗方法,甚至可以选用相同的方药。待续……作者:宋兴审校:宋兴金钊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欢迎原创稿,投稿请发送longanxichi@:点击关注我!
">北京看白癜风专科医院">北京治疗最好白癜风十佳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