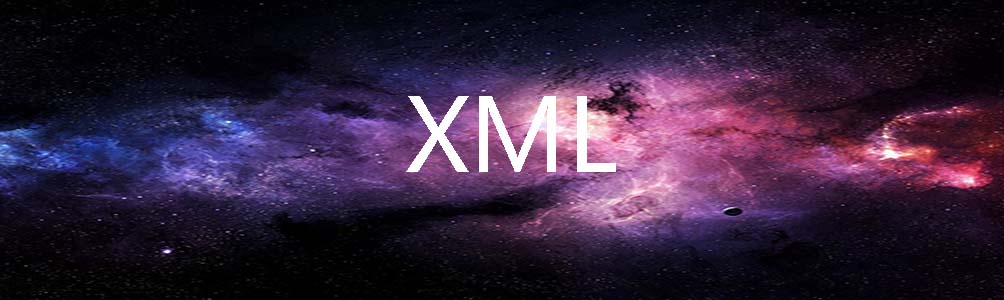猜猜蒋介石棺木里放了什么书
我的伯父姜必宁年出生在浙江江山城关,他的父亲叫姜安定,早年也是医科大学毕业,成为了一名优秀的药剂师。姜氏家族原是晚清时江山当地一个颇有名望的书香门第,伯父的童年就在城内市心街布政司巷有些破落的姜氏四合大宅院内度过。年,伯父18岁那年,还是个懵懂少年的他走进了上海江湾的国防医学院,成为当年该校全国六区联招百余名新生中的一员。年,国共战争时局吃紧,国防医学院于当年二月举校搭乘安达轮转迁台湾。刚读大学二年级的伯父遂仓促告别双亲,离乡赴台,就此开启了一段不平凡的人生际遇。寒窗多年,年以医学士学位毕业后,伯父任职台湾“三军”总医院(当时的台北“陆军”总医院)心脏内科住院总医师,从此投身心脏病学的事业。年考取奖学金,获得公费留英的机会,在英国医院专攻心脏学两年。随后又在年获得了美国卫生署国际博士学位后研究奖学金,赴密歇根大学医学院深造。两年后,伯父返回台湾,医院心脏科主任并在国防医学院担任内科教授。台北荣总是蒋经国于年为了照顾退辅及荣眷亲自创立的,医院之一。可想而知,发表过诸多重要论文并得到国际认可的伯父堪称台湾首屈一指的心脏病学权威。而更具传奇色彩的是,伯父从年开始,先后担任过蒋介石、蒋经国、严家淦的主治医师,长达二十年之久,被称作三代“御医”。
亲历蒋介石的最后岁月
年,42岁的伯父留学进修返台。当年5月,蒋介石的侍从医官发现蒋出现气喘、腿肿等心脏病的征兆,便向蒋夫人推荐了伯父。当伯父来到戒备森严的士林官邸面见宋美龄时,宋有些怀疑地说:“这么年轻!可以吗?”经侍从医官熊丸、陈耀翰的大力推荐,伯父成为蒋介石医疗小组的一员,开始了并不轻松的御医生涯。
阳明山后山松林隐蔽着一栋幽静的四合院回廊别墅,正是蒋介石常驻避暑的中兴宾馆(后改名为“阳明书屋”),伯父踏入官邸才两个月,蒋介石就在这处避暑官邸突发心肌梗塞。那是年7月20日,一个炎热的下午,蒋介石突感胸口不适,全身冷汗,神志迷糊,进入休克状态。当时在场的熊、陈两位侍从医官和伯父为蒋紧急做了心电图,确诊是急性前中膈心肌梗塞。于是在采取吸氧治疗、静脉注射强心及利尿药物等急救措施后,医院的十二位医师和十多位护士,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轮流值班看护。蒋介石发病当夜,群医会商,病人已出现合并左心衰竭,命悬一线,危在旦夕,便决定由卢光舜医师去纽约请旅美华裔名医余南庚教授到台湾会诊。
据伯父回忆,两位救星马不停蹄、风尘仆仆赶到中兴宾馆的那天是7月23日,经过检查,此时的蒋介石心肌梗塞并发急性肺水肿,实际上已接近弥留状态。虽然在过去三天里,医疗小组尽了最大努力,但病人的状况依旧是凶多吉少。当时,余教授想起一篇临床报告中以血管扩张剂治疗心肌梗塞合并急性肺水肿的成功病例,同伯父商量后,医疗小组果断采取了这项方案。静脉注射血管扩张剂约半小时后,奇迹出现了,昏迷了三天三夜的蒋介石,病情神奇地出现改善,神志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甚至能够说话表达。第二天早晨X光胸片也显示肺水肿已基本消失,蒋的言语、意识、饮食均逐渐恢复。伯父说起这些,不免感慨,当时注射新药剂的功效把蒋从九死一生中挽救回来,真是医学上的一个奇迹!伯父说,死里逃生的蒋介石对医生,尤其是余教授百依百顺,言必听从,是个十分合作的病人。有时到了吃药时间,不必护士提醒,他就像闹钟一样自己开口说:吃药!
但蒋介石从此卧病在床,半身不遂,无法办公,一切大事基本交由蒋经国主持。蒋介石的饮食起居都需要人帮助,直到年去世前的三年中,十二位教授级主任和护士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轮流在床侧值班,就连士林官邸的二楼会客室也被布置成护理病房,急救系统、氧气、X光机和各种检验设备应有尽有。而伯父作为心脏病专家,熟悉急救方法,所以在蒋病重时,即使不是值班也会留在病房或者官邸。
伯父三年间几乎每天进出士林官邸,亲历了蒋介石生命的最后时光,但他口风甚严,官邸讯息,连妻女都少有所闻,只是在荣退后才提起这些往事。根据伯父的观察,蒋介石生活非常规律,每天早晨六点,由秘书读报,接着做早餐祷告,之后蒋经国会前来问安并报告当日行程。然后蒋要接受医生的检查,并在护士帮助下服药。宋美龄和孔二小姐会来探视闲谈,有时也会让副官推着轮椅走走。到了晚上,在蒋介石身体情况许可的情况下,常会在走廊上播放电影或京剧。不过,他的体力只能看四分之一,所以伯父说他们在后面看得正入神时,蒋便叫停,等第二天晚上再看。
伯父回忆侍医蒋介石的轶事,说印象最深的是蒋对唐诗的爱好。蒋介石后来病重体弱,连捧书都很吃力,所以常让一位值班的护士朗读《唐诗三百首》。伯父在病床边值班,也就一同聆听。伯父说那位朗读唐诗的护士陆小姐嗓音清脆悦耳,有时遇见不认识的字十分窘迫,这时蒋介石就会教给她。后来蒋去世人殓时,蒋夫人和孔二小姐就是听从伯父的建议,把那本封面改用牛皮纸修补过的《唐诗三百首》放人棺中。
年4月5日是清明节,这在伯父记忆中是难以忘怀的,因为这天夜里,蒋介石心跳突然停止,伯父那天正好在士林官邸值夜班,他看到心电图在监视器上即刻消失,紧急抢救无效,这位中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就这样在睡眠中与世长别,享年88岁。
年5月,为了表彰伯父的工作贡献,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在士林官邸亲自给他颁发了“景星”勋章。
蒋经国猝逝,“冤情何时能了”
伯父的医术深受蒋家人的信赖,年到年的十年间,他又继任蒋经国的“御医”,经“辅导会”前主委赵聚珏推荐,挑起了蒋经国医疗小组召集人和主治医师的重担。谨慎的伯父担此重任,更是如履薄冰,食不知味,夜难安寝,一刻都不敢放松。尤其到了蒋经国晚年,病情危重,伯父现在想起那十年之间的“御医”经历,仍然觉得十分惶恐不安。蒋经国喜欢外出巡视,出访外岛、花莲等等,为了确保他的安全,伯父制订过一个“祥泰计划”,从台湾医学界调集精英,建立起一个台北地区以外的紧急回应系统,随时为蒋经国保驾护航。
蒋经国长期患有Ⅱ型糖尿病,有数十年之久,每天都需要注射胰岛素,而且到后期使用高剂量的胰岛素也已经无法控制血糖了。就因为这种顽固的疾病,他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伯父回忆蒋经国抱病的痛苦,说除了白内障,年,蒋经国的右眼视网膜剥落,接受了手术治疗,但效果并不理想,到晚年已经无法亲自阅报、批公文,体力也就此一落千丈。雪上加霜的是,术后不久,他的双脚也由于糖尿病并发症,发生了神经性病变,失去了知觉,脚踩在地上如同踩在棉花里一样,所以到最后,上床、洗澡、上下车、吃饭这些日常的行动都需要副官抱扶,无法完全自理。而最让伯父忧心的,还是蒋出现的心脏问题,不但有心律不齐、血管硬化,还出现了心衰竭,因此也安置过一个心率调节器。为此,伯父不仅要求蒋经国的医疗小组随时待命,还必须保证七海官邸二十四小时至少要有两名医师值班。伯父说,十年间,蒋经国住院数十次,他的病历就像一本百科全书,可见蒋经国晚年的身体状况实在不容乐观,几乎可以说是灯枯油尽。可想而知,作为医疗小组召集人和主治医师的伯父,他责任十分重大,工作极其艰辛,心里承受的压力煎熬更不必说了。伯父的女儿说起自己父亲在七海工作的阶段,提到在蒋经国去世的前些日子,父亲自己常抱怨胃不舒服、胸口郁闷,还去过中心诊所急诊,所幸并无大碍。
“御医”这个光环下,绝对是个苦差事,不单单是行医工作的辛苦,更有盛名之下外界的质疑和风波带来的难言之苦。
年1月13日这天早上,蒋经国起床后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有些恶心,但检查血压、脉搏和体温都还正常。然而到了下午,他突然大量吐血,迅速引发了休克和心脏呼吸衰竭。伯父他们医疗小组立即进行心肺复苏抢救,但已经回天无力,到下午3点50分,蒋经国病逝于台北的七海官邸,享年78岁。蒋经国因大量胃出血而休克猝逝,伯父说这种吐血猝逝的病例,在医学上其实并不少见,但由于当时蒋经国的病情一直对外保密,属于高度机密,医疗小组也始终守口如瓶,导致外界感到他的病逝十分突然,无法接受,整个台湾为之震惊。于是,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猜测,怀疑蒋经国的医疗小组,尤其是伯父“医疗疏失”,使他们蒙受难言之冤。那段时间也是伯父“御医”生涯中最难熬的一段。当时,不光是坊间各种传闻、媒体发难,“立法院”和“监察院”也群起对伯父和医疗小组进行质询。“监察院”特派酆景福委员组成专案调查小组,整整进行了两个月的严密审查。其间每天报纸大量臆测,虽然当时没有狗仔队,但记者们蹲守在伯父家门口、办公室、诊所各处。伯父只好同伯母坐邮轮外出散心,但心情沉闷,只说:“美景不美、美食不香,冤情何时能了。”好在最后终于水落石出,专案调查小组宣布医疗无误,蒋纬国和“行政院院长”俞国华也出来主持正义,这才还伯父清白,平息了这场风波,生活逐渐恢复平静。这当中的许多委屈苦衷也只有伯父自己最清楚。
回忆起在七海官邸工作的往事,伯父说“总统”待医护人员态度都很温和。在七海官邸,有客人时都会奉茶招待,而每次伯父去,蒋经国夫人蒋方良的贴身女佣阿宝姐都会特别为他泡一杯上等咖啡,送上新鲜水果。不过,蒋经国有时脾气很拗,工作中也有一些困难之处。伯父提到蒋经国失眠,每晚都要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入睡,偶尔因为第二天有会议或者军事演习,吃了一颗,但到了半夜一两点钟又会醒来,无法再睡,就会要求再吃一颗安眠药。伯父就用形状差不多的维他命来冒充安眠药。蒋没有发现,吃下维他命后居然也就安然入睡To伯父戏称这是“欺君之罪”,但是因为担心他第二天无精打采会打瞌睡,也就只能这么做。
作为蒋经国的主治医师,伯父对他的衣食起居也非常了解。比起蒋介石士林官邸饮食的讲究,七海官邸没有大厨,只请了军中服役的年轻厨师,做菜的技术很是一般。而蒋经国也因为糖尿病节食,在吃上从不计较,有时晚上肚子饿了,就直接让厨房做两只荷包蛋就行。在澎湖、花莲、金门外岛巡视,也是有什么吃什么。而女佣阿姐又十分节俭,外岛送来的黄鱼总是放在冰箱里等到快要坏了才拿出来吃。后来,伯父决定由台北荣总营养组长专门打理蒋经国的食谱,按照糖尿病饮食的热量规定计算准确,而且做的菜肴也比较符合蒋经国的胃口,这样才解决了他的饮食问题。令伯父十分心酸的是,蒋经国病重时,心力交瘁,但是却没有人可以分忧,蒋方良夫人不问政事,长子蒋孝文身体病弱,次子蒋孝武远在新加坡,唯一能在身边照料父亲的幼子蒋孝勇又尚年轻。至于亲密的朋友,原来还有“新闻局长”魏景蒙能和他说笑解闷,而魏景蒙过世后,蒋经国就更加寂寞了。伯父说他从没见过蒋做过新衣新鞋,也没有运动和娱乐,就连电视也不能看,接见重要官员都是在卧室床上,可以说是风烛残年,颇有几分凄凉。
“姜必宁奖”促两岸交流
伯父荣退后依然致力于培养后进,可谓是退而不休。年,经过台湾“财团法人心脏医学研究发展基金会”的深思熟虑和多番研讨,决定设立一项以伯父的名字来命名的奖项——“姜必宁奖——杰出青年心脏论文奖”,以此来鼓励后学。
伯父自年担任台湾“三军”总医院心脏内科主任,五十余年来,日新月异,他见证了心脏病学的发展。半个世纪中,伯父亲身经历了心脏病学的各项进步和创新:从心脏听诊器、心电图、心导管、超音波心图到核磁共振、心率调节器、心脏移植手术、冠心病安放支架等等,伯父在台北荣总和阳明大学都全程参与并领导发展。他慨叹自己能有幸亲身经历了大时代科技的跃进,更对未来医学的发展充满信心。然而,伯父欣喜于医学进步的同时,也常怀忧患之心。颇重医德的他以为如今社会的风俗演变已经使医界面临严重挑战,昔日医生牺牲奉献的精神和受社会尊重的典范日益式微。他担忧现在的青年医生好逸恶劳,毕业后往往抛弃内、外、妇、儿四大主科,转而争相投入医学美容、整容、皮肤、眼科等较少夜班、急诊而收入又相对较丰厚的工作中去。重利轻义、弃难求易,这在医者仁心的伯父眼里,简直是背离了良医救人济世的宗旨。伯父十分看重青年思维的活力和灵感,认为他们往往能够独辟蹊径,有所创见,从而获得最新发现。正因为这些原因,伯父才同基金会设立了“姜必宁奖”,将这称作“心脏挖宝计划”,鼓励青年医师创新研究工作,选拔人才,为人类健康作出贡献。获奖青年每人将获得一笔数额不小的奖金,伯父希望这能帮助优秀的年轻医生,消除后顾之忧,不要因为资金等原因放弃理想。
年,为了促进两岸心脏学术交流,基金会董事会决定,增选大陆区(包括港、澳)获奖者一名,并且在当年12月1日在厦门举行的第三届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心血管专业委员会年会暨第四届海峡心血管病学论坛上颁奖并宣读获奖论文。医院的医师,华中医院的程翔博士因其在心肌缺血再灌注损伤上的一项研究得奖,成为了大陆地区首位“姜必宁奖”的获得者。而在这次年会上,也实现了两岸四地首次同步直播。
伯父此举是两岸关系进程中医学领域重要的一步,这个奖项只是一个开端,借此希望能引导两岸的学术研究合作,加强两岸的交流与联谊。跨世纪的流浪
年,年逾古稀的伯父为了纪念入学“国防”医学院六十周年,写过这样一首小诗《流浪之歌》,里面有这样的语句:
在你尘封的记忆里,
此刻是否浮现起那战乱的一章?
六十年前,青春少年,踏上惊涛骇浪的远航,
挥别江湾,安达轮横渡海峡,驶向台湾。
从此.
开始流浪,远离家乡……
莫问我来自何方。
我有一个遥远的故乡,
梦回江南,杨柳堤岸,
晓风残月,烟雨夕阳。
而今,
少年白发,人老异乡,
今夕何夕,才相会明朝又将分别,
似浮萍漂荡,
千山万水,地老天荒,继续流浪,
世事棋局茫茫……
伯父这一代人经历过上世纪那段动荡的烽火年月,从大陆横渡海峡转移到台湾,即便早已成家立业,仍然无法摆脱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浓重乡愁,“流浪”这两个字在伯父他们的心头是很沉、很沉的。伯父自己就说这种四海飘零的航程可能驶向一个自己以前始料未及的远方,而且往往没有归程。
在我还是个孩童时,爷爷就常对我讲不知大伯现今在何方,但一定会是个好医生。上世纪70年代初,家人意外收到了伯父的第一封信。我第一次见到伯父是在年,大伯携伯母回大陆探亲,大家聚在锦江饭店,而此时距离我爷爷离世已经多年了。
年4月,清明节后一天,伯父同家人来到杭州西湖。春天正是西湖一年中最美的时候,桃花盛开,杨柳夹岸,湖水荡漾,游人嬉戏。然而,伯父的心情是矛盾的,胸中凝结着忧郁。年,他即将随国防医学院远迁台湾,于是在腊月年底从上海江湾回杭州向父母辞别,数周后就要回校乘安达轮渡海赴台。回想起当年告别至亲的场景,伯父历历在目。当年,他和父亲在奎元馆吃了面,晚上在湖滨公园雇了一条船,绕湖游了一圈,在平湖秋月登岸陪父亲一道喝茶话别。第二天早晨五点多,天色刚刚亮,伯父为了赶上早班车回上海,匆匆离家。临行前,母亲送他到门口,眼里已经满是泪水,千叮咛万嘱咐,还让伯父把前一晚交给他的金戒指好好保存以备急用。伯父听完母亲最后的交代,点了点头,转身离去,不敢也不忍再回头看,直接往城站登车而去。那一年,伯父才19岁。年少的伯父就像平时离家赴校一样,对这次离乡赴台并不太在意,以为只是时局紧张暂时避难,想着也许放暑假时就可以回杭州看望父母。可那时的他,不会想到,这一走就是半个多世纪,当日的青年学子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而自己匆匆告别的父母早就驾鹤西去,如今只能空拜西湖之畔南山公墓中双亲的坟冢,真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啊!当伯父带着自己的孩子故地重游,半个世纪前永诀的那一幕一定时时涌上心头,就像一场噩梦猛醒了过来,只是梦醒之后,早就人事俱非,令人悲从中来,哀恸万分。伯父感慨命运是如此残酷,上了那艘安达轮便是一生,那一别便是永别。等再回来时是五十多年后了,双亲墓边栽下的松树已经长成了,合抱之木。他感慨未料到这半世纪的生离死别,就在那杭州车站与江湾码头。经历了跨世纪的流浪,人老他乡的伯父,想起母亲送自己到门口,那依依含泪的眼神竟是最后的一瞥。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同我的伯父一样,经历了这样跨世纪的流浪,背后有种种不堪回首的辛酸往事,但我们都深深明白:这个世上所有的暂别,假如遇到乱世,那就是永别。
重续的亲情弥足珍贵,和伯父恢复通讯后,我们通过书信与他通讯,父亲还把已经高血压过世的奶奶仅存的照片翻拍寄给伯父。同样患有高血压的父亲把在上海检查的心电图、药方寄去台湾,请伯父给予建议。年,父亲心梗抢救回来后,医生告诉他心脏受损脱落的膜可能会堵塞动脉,父亲因此情绪十分低落。后来伯父到大陆探亲,看了父亲的病情资料后,嘱咐父亲坚持按时服药,安慰他心脏脱落膜堵塞动脉的概率极小,大部分会在血管末梢被吸收。听了伯父的话,父亲减轻了心理负担,心情明显好起来。
年伯父来北京看奥运会时,年事已高,体力渐衰,此后就很少出远门,我们便通过邮件往来。我在新加坡工作的时候,每逢圣诞、春节都会给大伯寄去贺卡问候,伯父也会回寄贺卡,还时常会寄来有他的文章或由他审定的刊物、心脏保健科普书等。不久前,台湾知名音乐家李泰祥过世,伯父邮件发来评论文章和齐豫演唱的《橄榄树》。他在信中写道:
三毛写《橄榄树》描写了流浪者的心声与衷情。“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在宝岛上,有许多流浪者,他们因为不同的命运而流浪,历尽悲欢离合的沧桑,这流浪没有归程,乃是一个宿命。
本文选自档案春秋
欢迎热爱乡土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