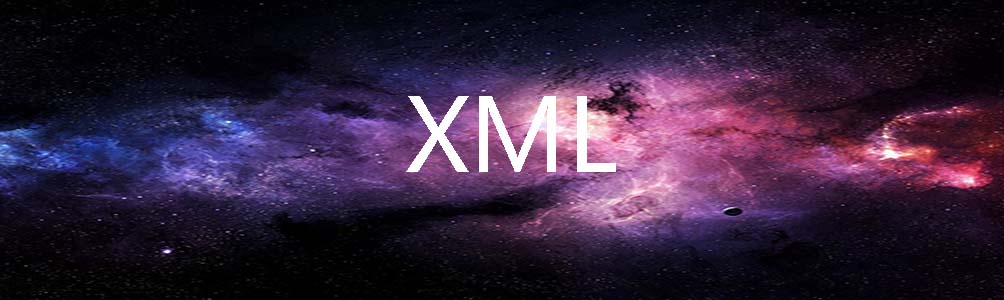原创储朝晖眼病与修炼
每个新生儿出生后睁开眼,就会对光产生条件反射,并渐渐通过双眼认识到千姿百态的世界。
我能记住自己用眼看到的童年生活情景,至今历历在目,家门前的小溪、池塘、水竹林、柿树。由于出生在桃花盛开的季节,每逢过生日,父母总要用各种方式表示一下,或许此举能激发内心的兴奋,所以对桃花的热烈的印象特别深刻。由于门前屋后都栽有柿树,所以家住的地方被人们称为柿树湾子。每年秋天青柿子被人家买去榨油用来做雨伞、斗笠以后,家里能获得一点收益,树枝上还多少残存一些,经过霜打日晒,到了冬天便黄澄澄的,不仅特别好看,还特别好吃。所以对柿树的印象也特别深刻。
童年生活在大别山腹地,四周山山相连,山中千奇百样的动植物,村中居民质朴、贫寒,还有那个时代热火朝天的运动。这些都通过我的双眼,形塑出我的童年人格。
不幸的是,童年我就感觉到并非是你想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每逢春冬季节,寒风刺骨的时候,我总是常得红眼病。每次发病的时候,总好像风把什么东西吹进了我的眼睛,于是就眼红、流泪、发胀、看不清外面的东西。限于当时的条件,也得不到有效的治疗,只能任其发作,待到它自己自然好了为止,父母实在想不出办法的时候,只能拿热毛巾帮我捂一捂,或根据乡间传说的用香油炒汤圆吃,或找点大葺子草煎水喝,母亲为了弄到这种草,到四乡八里去讨要,或到传说有生长这种草的沟沟壑壑搜寻采挖,花了很多时间才有少量的所获,煎了水喝下后效果并不明显,我只能趴在家里的长凳上,熬过那艰难的日子。此时我的眼睛不能够看到什么,脑子里就翻腾着,漫无边际的想着不能通过眼睛看到的东西,总期望构建一个不需要通过眼睛也能感知的世界。随着想像的东西越来越多,渐渐的感到不仅通过眼睛的感知,可以塑造我的内心,想像同样在塑造我的内心,看不见的病眼与健康的眼睛一样都在以某种方式修炼着我。
上中学后,才发现我的眼睛和其它同学不能够比,黑板上别人能够看见的字,我看不见,高考之前测的视力还有1.2,而其它同学大都1.5有的甚至2.0,这是我第一次从客观实证的数据感受到自己眼睛与别人的差别。进入大学阶段,为了能看清黑板上的字,不得不配上了我的第一副眼镜,不料此后的视力,越来越差,近视的度数也越来越高,换眼镜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从戴度加散光,逐级上升。
起初认为视力的变化仅仅是视力的问题,后来越来越感觉到是跟自己的人生取向相关,当你喜爱什么的时候,你就会为了什么拼命,当然包括不顾自己的视力损伤,成年后,第一次大的视力衰退在到年其间,当时因为自己喜爱做陶行知研究,又被分派作为《陶行知全集》(川教版)专职编辑和编委,负责到各个图书馆查阅资料,每天早出晚归,早上尽可能赶在图书馆开门前到达,中午凑合着吃点面包,下午在图书馆停止发书之后,再赶回住处,才发现自己两眼昏花,可能是饥饿,也或者一天当中用眼时间过长,用眼的时候把精力聚集在所看的内容上,一歇下来疲惫就袭击上来。中间为了充分利用时间,要尽可能快速扫读,在众中的文献资料当中,寻找与陶行知相关的内容。当时所查阅的主要是年到年的旧书报杂志,大多数已经发黄,翻开就一股呛人的味道,看起来十分费眼,尤其是年到年其间的报刊,由于处在抗战其间,纸料和油墨都很差,字迹不完整,通常为了看清一二百字的文章,花费二到三天的时间,依据不完整的字迹反复猜读,就这样四年下来,收获了《陶行知全集》的出版,让我们当时参加这份工作的同事都兴奋不已,我的视力却从1.2,降到了0.8,换了眼镜,仍然感觉视力在下降。
第二次视力下降出现在0年以后,经过十几年的教育与社会调查,已经很明晰的认识到,中国教育的问题所在,并找到若干突破点,试图从学理上去解决问题,比如大学精神与现代大学制度,教育管理和评价,也就不顾一切的投入。加上此时已有互联网,可以在网上查阅大量的资料,撰写文章,回应社会关切的教育问题。社会对教育问题解决的需求大量增加,即有官方的,也有民间的,媒体的,研究机构的,我本着说真话,少说套话,空话,假话的原则,尽可能予以回应,每次的回应也都尽可能的谨慎,客观。于是又需要阅读大量的资料,全面的掌握信息。各方面把我推到一个不能停歇的运转状态。加之阅读和写作所面对的介质都由纸质转向电脑屏幕,于是眼睛受到巨大的伤害。
年8月原订安排了一次先后到马鞍山和江西上饶的教研活动,后来由于台风到来,取消原定飞往南京的航班,提前于8月8号坐火车赶到南京,在马鞍山活动后。8月10号乘火车从南京到鹰潭的过程中,由于景德镇被水淹了,火车在芜湖的湾里停止不前,等待两小时后,车站宣布此趟列车停开,让旅客自行选择改成其它列车离开,整个火车站乱作一团,忙乱中挤上一列从沿江铁路开往南昌的火车,可是原来的卧铺没有了,车厢里人挤人,站了一夜,次日早上到达南昌的前一站,才找到了一个位置坐了一下,接着赶到上饶,15日从上饶回京后,右眼就出现了飞蚊,19医院就诊,医院眼科技术不好,检查之后,没有指出接下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只是给点眼药水和药片了事。
由于没有解决问题,眼睛的状况越来越坏,医院医院就诊,这对于在体制内工作和生活了二十七八年的我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此时才切身的感受到自己的眼睛是比公费医疗、工作身份、单位关系更切近的存在。医院的眼科开张转院单,他们说我医院,不能随意开转院单。当然我也听说过别人走关系开出过转院单,可是我的眼睛已经有病了,还有日常工作,原本就没有多少时间来找关系,更何况找这种关系需要低声下气请客送礼,这些都与过去已经行成的人格和行为方式格格不入。
既然开不出转院单,就只能考虑放弃公费医疗,医院医院治疗。然而自年大学毕业工作以来,就把公费医疗当作自己可享受的一块巨大福利,此前因为没有得过什么病,几乎不用,也很少报销,现在轮到要用的时候,却发现用不上。原来被众多人羡慕的公费医疗体制,却不能给我的眼病有半点益处。只能修改自己形成几十年的意识,大胆的到国内医院排队就诊。
可连续两天早起,都无法挂上号,直到9月28日,右眼上下两个方向出现类似西瓜瓤的障碍物,并不断的扩大,这种情况从未有过,此时感觉眼睛应该有大问题了。适逢十一假期,医院不开诊。一家人在郁闷中度日如年,几乎每隔一两个小时,就对着镜子看病况的发展。可是只见恶化,不见好转,似乎越来越绝望。
爱人情急当中,网上医院有半天的门诊,四医院挂号处,依然是茫茫人海,怎么能挂上号,是面对的困境,爱人提出找号贩子买,我却犹豫不决,此前形成的循规蹈矩的人格再次遭到重力撞击,无奈之中,爱人豁出去了,通过号贩子,终于拿到了一个门诊号,谢天谢地!我的人格还是完整的么?
医生一看就诊断为视网膜脱落,急需住院手术,而医院十月八号才正式上班,还要苦等四天,四天中,内心里倒海翻江,原来计划好的事不能做,眼睛里灼热的疼痛,只能从缝隙中看见一丝丝光亮,却很难从这点光亮中看到希望,对过去的自己进行反复的梳理,总有许多想不明白,看不透彻,想对过去的自己进行修正,又不知从何着手。想对社会进行思考,尽管有三十多年的社会调查,依然乱做一团。
漫长的四天终于过去,8号试图去同仁去登记住院时,得到的答复是住院部病床客满,排队最快也要三个月以后了,这可怎么办,三个月后,视神经都枯萎了,还怎么治,还有眼睛么?我的人格再次被巨浪拍打在沙滩上,医院门外散布着众多专家号,住院号的叫卖者,声称:“只要,保证医院”,这都怎么了?对此,我难以接受,也难以拒绝。内心的病疼似乎比眼睛更历害。于是还是不得已的选择似乎更为体面的方式,托人找关系,总算有贵人相助,十月十医院的特殊病房。
接下来为做手术是不是要送红包纠结,爱人说,一定要送的,不过她从没有送红包的经历,主张每个参与的医护人员都送千八百元,我当时就感到,这方式不行,送的不恰当还不如不送。无奈之中,只能找原医院熟人打听多少合适,对方说:“如果没钱就给五千,有就多给些”。爱人准备好了红包,盯着主治医生的行踪,总算找到一个她单独进休息室的机会,赶紧凑上去准备出手的时候,被对方推辞了。不收红包,手术会做成什么样呢?
后来的观察发现,这位主治医生并不是不收红包,本人就亲眼看见,有人就嘻嘻哈哈请她对某个病人关照的同时把一个大大的信封放进了她的白大褂口袋,她受着若无其事。也有其它人在诊室里送礼被笑纳。前后一分析,原来她只收信得过的熟人,或者干脆不认识的生人钱礼,如果有人介绍,又不很熟悉,则有可能拒收。十月十五日进行了,视网膜脱落的手术。接下是真正的考验到了,遵照医嘱,要一天二十四小时趴着,以保持手术中打入的硅油处于水平状况,支撑视网膜的恢复生长,这不仅是体力的考验,耐力的考验,也是心态的考验。既便是站立也需要低着头,平常习惯向前看的眼睛,只能够看到脚下的地面,视野也大大压缩了。内心的空间也跟着变小了,即便人有多大的心向,也不由得不低头走路,看到现实。
手术前医生说,可能采取打油或者打气两种方法,我表示过希望打气,可是手术进行中,医生选择了打油,这就使得后来还要排队到同仁再做一次取油的手术,按正常的程序第一次手术后三个月取油是合适的,医院的床位总是紧张,医院说好到时候通知取油,三个月后我们就打电话问,什么时间能办理取油的住院手术,得到的答复,等就行了。我们也不想再次突破规则和做人的底限,找人托关系。可是这一等就等到了年的6月才通知入院取油,对方还直问:“你到底取不取油了,这么长时间还不来”。似乎我们遵循他们白纸黑字的规则,没有托人找关系或者用钱买通号贩子还是我们的错。由于间隔时间过长,打进去的油已经变成了乳化状态,取不干净,直接影响视力,以至术后的视力一直较差。这个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再一次修理了我的人格。
后来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家画卷》有一本《陈寅恪画卷》在审稿当中,我惊奇的发现一个细节,陈先生的眼睛第一次发现问题,是在四十八岁,而我的眼睛第一次住院治疗也是在四十八岁。这让我很伤感,陈先生是个大学问家,我也立求在喧闹的社会中静下心来做些学问。自感与陈先生的学术天赋相差太远,却不幸与陈先生在相同的年龄患上眼病。这究竟是生命当中眼的使用节率,还是天命?
原本想做完手术后,可以潜心做自己的研究,不料好景不长,年到沈阳师大参加该校学术论文答辩,眼睛再次发炎,到当地的何氏眼科检查,医院的诊断不仅是发炎,还说是患上了白内障,需要做手术。自己也感觉到视力在不断的下降,原来不知道原因,从此自后,又知道自己的眼睛又多了一个毛病——白内障,尤其是以前做过视网膜脱落手术的右眼。
从沈阳市区到机场的路上,望着车窗外太阳映照下的雨点,似乎是老天又在给我一种预示,希望中总是掺杂着痛苦。考虑到手边接受到各方面的委托,有几本书稿的任务,就想凑合凑合,只医院治疗。
直到年初,几本书稿基本完稿,交于出版社。家医院做手术,医院和医生,找到一位做过上万例白内障手术的主治医生,于年4月23医院。这次住院,原本只想对右眼进行白内障手术,可是在手术前准备的时候,主治医生力劝把左眼同时也做了,我辩称:“左眼不厉害,等段时间再做”。医生说:“只做一只眼睛,由于驱光率不同,会发生两眼所看对象大小不同,位置不一的现象。”当时我也就随和了。待右眼做完手术的第二天,摘下纱布,发现对视力改善不明显,我再次对医生提出左眼暂时不做,医生说:“做吧,做吧,已经做了准备了”。于是勉强上了手术台,原本只需要十分钟的手术在手术台上出现了意外,医生在把我原生的晶体超声波乳化抽出后,正在放入人工晶体的时候,连问三句:“你的眼睛怎么这么大”。当时我并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医生接着:“你的这个晶体膜比较大,人工晶体放进后是飘浮的,你看怎么办。我把你抽出来吧”。由于此前从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手术前医生告知情况的时候,也没有提起这种情况,理智告诉我手术台上,只能由医生做决定。于是我回答说:“你是医生,只能由你决定”。医生把已经放入晶体膜中的人工晶体抽出来,由于操作的时间比正常的手术时间长,我感到疼痛难忍,全身虚汗,医生把我送出手术室时说:“不要紧,不要紧的,回家休养一个月后再置入晶体”。
走出手术室门,医院原本安排与做其他同来做手术的人一起送回住院部,可是我已经虚脱的站立不住,只能就近找个地方躺下休息,其它医生找来止痛片,休息了一段时间后,用轮椅把我从门诊楼推回到了住院部。当天主刀医生又吩咐其它医生对我的眼睛进了多次检查,第二天,他自己也来进行专门检查,反复验证是不是已经造成视网膜脱落,当时没有显示出这种迹象。次日,主治医生在准备休五一假去上海之前,医院,对我进行专门检查。这次手术过程中出现的意外,在住了两天后,医院的出院证明中则表述为“手术成功”,我带着没有晶体的左眼回到家中休养,也带回一只没有落地又不知道何时落地如何落地的靴子在心上。
回家休养中,反复思量,医生在做手术之前对我的晶体膜,已经用仪器做过精细的测量,并记录在案,对我左眼的高度近视,晶体膜要比普通的晶体膜大,也是知道的,怎么到了手术台上才发现我的晶体膜这么大,这是我怎么也想不通的。另外,为何医生那么积极主动的劝说病人将自己认为严重程度不高的眼睛也做白内障手术,好为人医与好为人师,可能有相同的动机,也自然会衍生类似的结果,这个结果改变了我眼病治疗进程,也牵引了我的心路。从医学角度看,什么样状态的白内障最适合进行手术治疗,也应该有定数,不能简单以“反正是要做的,不如一次做了吧”来劝说患者。这种主观积极作为又一次“修炼”了我对医学作为一门学问的认识。
由于这样一个变故,数月前就订下来的日程安排,不得已一一改动或取消或推迟或换人。一个月后的5月23日,上午完成了北师大博士论文答辩后下医院,这次医生做了比上次手术更多更细的术前准备,并告知由于上次晶体膜囊袋损坏,只能采用悬吊的方式置入晶体,术后有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其中一种就是视网膜脱落。这次手术大约做了一个多小时,医生使用各种尽可能使手术做得完善的手段,我自己感觉到也是一次深刻的体验,且是我第一次做手术后向医生要止疼片。术后的左眼视力能达到0.3正好能看清一般书本上的五号字,似乎很适合我的工作对视力的要求,但是由于六七月份天气变化无常,我的视力受此影响,不很稳定,数次发炎,只能靠点氧氟沙星眼药水来消炎,而我单位医务室却没有这种药水,只能用效果不好的氯霉素滴眼液,使得这段时间的眼睛一直没有进入正常的状态。
五月底手术住院其间,在一次眼球偶尔的转动中,发现我的左眼右上角,出现了年我的右眼视网膜脱落时曾经时出现的阴影,但是在后来的反复转动中又不曾不出现,当时以为是虚惊一场,不料在手术后不到三个月的八月十三日,它真的成了事实。那个曾经出现阴影的地方,开始扩大阴影的面积,一下子就看不清眼前的文字或者是即便看得见也是变形的,此时才真正意识到不妙,但当时正在贵州乡下,又不医院就诊。原本是订了十五号下午回京的机票,医院挂号难的教训,立即告知家人,尽快挂号,幸运的是爱人通过平台医院的副主任医师门诊,同时也挂上了北医三院十九号的门诊,还与此前做手术的空军总院眼科联系上了。
十六日一早,到协和就诊,接诊的医生仔细检查以后,对我说:“你的眼睛肯定是要做手术,但手术很复杂,最好是找一个更有经验的专家,或者此前给你做晶体悬吊手术的医生做,他熟悉你手术的位置。”我当时就表态说“相信您能做的,我们就认定您做了,我们希望的只是能尽早尽快手术”,对方回答:“最快也要到下周三(8月24日)了”。走出协和,心思未定。十七日医院,挂了眼科主任的门诊,主任说:“你的眼睛再做手术确实很复杂,而且我们这里只能打硅油,没有气。如果打油,由于晶体的后膜已经没有,油会渗到晶体的后面污染晶体,造成视力不好,还是建议你去协和做。”无奈之下,医院复印了前两次手术的所有病案后离开。十八日上午,我们再次到协和做了所有的术前检查,发现原接诊的医生下午一点半出诊,便等到了一点半钟后将病案交给她看上次手术的详细记录,对方还是建议我们找经验更丰富的专家医生看,并开出了专家名单。说:“如果你们找不到人,我就接手做。”十九日上午,我们又到了北医三院,接诊的医生检查了下眼睛,又简单的问了几句,就说“要做手术”,我问:“是打油,还是打气。”对方说:“只能是打油。”我问:“打油的依据是什么”。他说:“手术复杂就得打油,手术简单就打气。”事实上因为北医三院此前打气出了事故,停止用气了。这种对话氛围,让我们无法接受,于是只能转身离开了三院。回到家,我们想方设法总算联系到协和眼科最有名望的医生并于医院托人加号挂上了他下午的门诊,这位专家看后说:“肯定要做手术,不做手术会失明。”我问:“什么时间能约您做手术”。他说:“我们帮你加急”。我问“加急能在什么时间能住院手术”。他说:“最快的时候是在两周后。”此时,医院首次接诊医生的通知二十三号入院的电话了。所以等到他看完所有病人后,上去问“我二十三号可以入院,能不能请你做手术”。他说:“那位医生能做的,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帮忙提意见”。接着匆匆赶去开会去了。
八月二十三日,医院眼科住院部,二十四日原定下午的手术,五点钟才进手术室,九点半出手术室,整整四个多小时的时间内,医生做得非常小心谨慎,边做边发现眼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确保打气没有泄漏,缝好的线头也一根根拎起检查看牢不牢。
手术后第二天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回到童年生活的村子,山体和村子的走势还是一如从前,村舍和景物却少有变化,屋前一村妇在用木盆洗衣,旁边有儿童游戏,屋内放有八仙桌,墙上贴有中堂字画,屋里的人我一概不认识,当我试图上前向他们说明我曾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时候,对方皆愕然失色,我感到悲从心起,嚎啕大哭:“妈,妈,我妈呢”,直至醒来,回想刚才的梦,或许是手术触动神经勾起童年早期的记忆,但半个世纪后,世事已变,再难以回到当年。
回想自己眼病发展的历程,自己当为它负第一责任,以佛眼观之,就是自己的眼睛难以承受起自己心愿的压力。一九八一年以来,我唯一的心愿就是希望以专业的方式把教育办得更好。当下,这个心愿具体为几个方面:一是感到中国教育没有办好的体制性原因是政府包揽,所以下决心要做中国现代教育社团史丛书,把一八九八到一九四八年间教育社团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展示给当今,期望能为未来的教育专业社团发展提供一面镜子,为改善中国教育提供组织资源。二是继续完成在大学精神方面的研究,在已经出版的两本大学精神专著的基础上完成《大学精神论》的写作。三是写一本细统分晰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未能发展好的根本性原因的著作。再就是回应各方面对教育问题的追问,由于几十年来一直在做社会调查,每次遇到被调查人,他们对教育的疑惑期待着我的回应,我一直感到有难以抛却的责任和使命。
事实上我的心愿,不止是我的心愿,是众多人的心愿,不同的人愿愿相结,形成一个连环,连环中谁的态度积极,平衡就可能从谁哪里打破,他所承受的压力自然会比其他人大。实现这些心愿,当然不只是靠我的眼睛,仅仅是因为我长期 在治病过程中,天天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接触,深刻体验到他们的痛苦与诉求,困难与期望,真是应了民间的一句话,有什么别有病,一个得了病的人,除了去求人,更多的还是只能改变自己,调整自己的心态,降低自己的期待,改变自己原来对事与人的看法。面对现实,我再也不能看到从前所能看到的那么多内容了,几十年坚持的用集成人学的方法研究教育也需要做些修改,对所想写的内容也要做大量的精减、筛选,需要更加勇敢的对别人的要求说不了,甚至很惋惜此前过于冗余的使用眼睛,看了许多不必要看的内容,耗费了宝贵的视力。
许多朋友劝我干脆什么也别干了,什么也别看,也就是通常人说的“放下”,从逻辑上说我能很清楚的理解,“放下”是彻底的解脱,可是真要放下三十多年积累起来的梦想,也难以做到。只能选择放下尽可能放下的,留下尽可能留下的。对此主观判断和现实可能之间没有明细的边界,以至我还难以逃离苦苦求索之旅,仍在修炼之中。
原以为学校是教育修炼人的地方,医院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修炼着病人以及家属和医护人员。一个社会中这种人群的修炼状态,标志着它的文明状态。我的眼病还在继续,以有的经历让我深刻的感受到,如果你没有得过什么病,没有为治好自己的病而奔波求过人或反求诸己,你就没有真正的修炼过。
年9月3号
储朝晖,男,年出生,安徽岳西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专业教育硕士,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史专业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教育史研究》副主编。中华教育改进社理事长。
善言亮语由安徽商报新闻中心副主任陈亮,青年作家李多善倾力打造的自媒体平台。集百家之言,邀万人溶栓宝之老年痴呆症状有四不护士资格考试易混搅知识点口诀难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