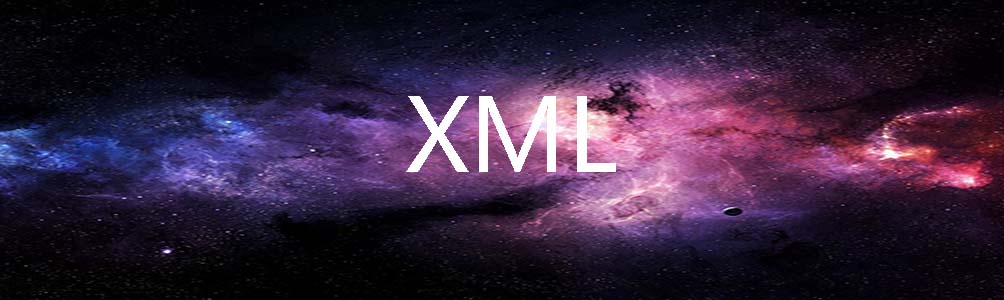纪念焦菊隐先生110周年诞辰焦菊隐最后的
至今人艺演出的剧目中,仍然可以看到焦菊隐无所不在的灵魂。
主页君按
今天是焦菊隐先生周年诞辰,特刊发梁秉堃先生的回忆文章以为纪念。
“你们还懂不懂剧院的规矩?”
年的春天,我被调到北京人艺灯光组来工作。刚来没几天,听剧院邵惟秘书长的介绍——剧院有一位副院长是全国赫赫有名的大导演,他叫焦菊隐。又听到同事说,大家都尊称他为“焦先生”,是一个脾气不好,相当严厉的导演,有时候在排练场上,只要他一拍响导演桌上的手铃准备开始排戏,站在布景片子后边候场的演员,还没有上场两条腿就一再打哆嗦;有时,对演员的表演不大满意,焦先生竟然会大声喊着:“你再上一次场,如果还不行我就换人!”……为此,我很想见见焦先生,可是作为普通工作人员,又是一个小青年,一直没有机会。 大约一个月以后,一天,我和灯光组的范贵山被派到北京剧场去取灯光器材。 当我们走进观众席的时候,里面是漆黑一片,只有舞台上亮着工作灯,原来是正在排戏。 范贵山告诉我,灯光器材都放在乐池里。于是,我随着他走到舞台前面的乐池边上,迈腿翻越铁栏杆,下到里边去。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样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然而,我们刚刚下到乐池里站定,就突然听到观众席里有人大声喊着:“刚才是谁下乐池里去了?哪位啊?”说话的语调、语气都是很激动、很强烈的。 这时,我仍然没有意识到是在说我们。 接下来,那个声音更大了起来:“演员先停一下!”排戏被停止了,我这才有点儿明白,同时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个声音继续喊下去:“你们还懂不懂剧院的规矩?现在是在排戏,怎么可以在这种时候随便走来走去?还从舞台前边迈栏杆呢?” 范贵山大约看到了我脸上莫名其妙的表情,用非常小的声音说:“是焦先生!” 我当时真有点儿吓坏了,可是出于好奇,又不由得扒开乐池铁栏杆上的黑布缝儿,极力向外窥视着。由于观众席里没有光亮,只能靠着舞台上的余光折射,才模模糊糊地看到,在观众席里七、八排中间,坐着一位身穿深蓝色呢料中山装,梳着整整齐齐的光亮头发,清秀的脸庞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长者,手里拿着一支点着了的香烟,样子显得有些不平静。“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也不管是谁,如果是新来的人,就应该好好学学《演员道德观》。”焦先生不断挥动着手,“剧院里所有人都应该懂得并且记住这样一条不可动摇的规矩,那就是——剧场,是艺术的殿堂。不论是排练的时候,还是演出的时候。” 我和范贵山低着头,老老实实地听着,在乐池里连一声大气儿都不敢出。 焦先生停了一下又说:“好了,演员往下接戏吧!”舞台上又继续排戏了。 由于焦先生发了火,我和范贵山再也没有敢从乐池里走出来,虽然已经找到了灯光器材。就这样,我们在乐池里边“猫”了一个多小时,一直等到上午排完戏。 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了剧院严肃的工作作风,也是第一次认识了严厉的焦先生。
最后一次难能可贵的、难以忘怀的表态
年,北京话剧团(北京人艺在“文革”中被迫改成的名字)排练了一个歌颂农村干部王国福阶级斗争精神的话剧《云泉战歌》,当时上边来了一个新精神——对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要实行“一批、二用、三养”的政策。于是,剧院“军工宣队”准备征求一下焦先生对这个戏的意见。 焦先生这时已经离开了“牛棚”,刚刚放到群众当中去继续接受监督和改造,接到看连排的通知以后,一位和他关系不错的演员(也是他的学生),马上来到他住的小平房里以好言相劝。 演员问:“您真要去看连排吗?” 焦先生答:“要去,不去是不礼貌的。” “看完以后,您还要发表意见?” “那当然。” 演员想了一下说:“如果非去不可,我提出三个办法供您选择——第一,是看完戏以后一言不发,这样他们就抓不住您的‘辫子’,顶多说您不够积极;第二,是光讲好的方面,一个字也不要批评,他们顶多说您有顾虑,不诚恳;第三,是凭着自己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想到说什么就说什么,这可能是最危险的。” 焦先生听后一阵沉思,没有吭声。 演员继续说下去:“我不希望您选择第三种办法。因为这种办法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即使暂时不批您,也会记下一笔账,以后是随时都可以拿出来敲打的。” 焦先生抬头问:“你说完了吗?” 演员点点头:“完了。” 焦先生向演员笑了笑,还是没有吭声。 演员看得出焦先生是要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为此心里不由得有所担忧。 焦先生看《云泉战歌》连排的那一天,特意换上一身衣服——一件半旧的灰色毛料中山装,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连裤线也是笔直笔直的。而且,如同以往一样,头发也梳理得一丝不乱,乌黑发亮。他走进首都剧场后楼的三楼排练厅,来到最后一排座位上,和一些演员一起看戏。 连排结束以后,并没有人征求焦先生的意见,他对此也不在乎,便自自然然地回到史家胡同宿舍大院那间又阴冷、又黑暗的小屋里去。 第二天,“军工宣队”派人来找焦先生谈看戏的观后感。焦先生认真地想了一下,说出:“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这些话在“文革”当中,出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之口,就像爆破了一颗原子弹。听意见的人顿时惊吓得目瞪口呆,并且深为焦先生捏了一把汗。 这个严重的政治和艺术表态很快就上了剧团的第13期《情况简报》,当作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反攻倒算”的突出事件,既上报,又下发。 那位热心的演员马上找到焦先生说:“您可捅大娄子了!三种办法您为什么单单选了最坏的一种呢?”焦先生似乎是有所准备的,缓缓地解释道:“我这一辈子都是凭艺术家良心办事的,你跟我排了不少戏,你应该了解我,我知道你的办法都是出自善良的愿望,谢谢你对我的关心。至于‘军工宣队’对我的意见有什么看法和打算,我是根本不作考虑的。” 这就是焦先生一生当中,在戏剧问题上最后一次难能可贵的、难以忘怀的表态。尽管他那时已经被剥夺了一切从事艺术活动的权利,但是凭着艺术家的良心,对一个所谓“三突出”的剧目,竟然提出了公开的、尖锐的、不留情面的批评,实属既有胆又有识而难能可贵。
焦先生常常在内心痛苦难以控制的时候,跑到北京城墙根儿大哭一场
到了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高潮中,焦先生在北京市文化系统于北京展览馆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再一次被“毛泽东思想解放军、工人宣传队”的负责人点名批判,并定性为“为30年代反革命文艺黑线翻案,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新生事物”的、顽固不化的、死不改悔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为此,焦先生这位曾以“南黄(佐临)北焦(菊隐)”闻名于全国的,甚至全世界的,立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戏剧事业的,并在话剧事业上已经做出了开拓性、历史性、突破性伟大功绩的人,竟然两眼闪着晶莹的泪花,万般无奈又悲愤满怀地向友人说:“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恐怕再也不能做导演了!” “文革”后期中的一天清晨,焦先生心灰意冷,在无处可走、无人可叙说的情况下,来到前夫人秦瑾的家里。 他们相对无言,停顿了许久以后,焦先生说:“老舍跳太平湖自杀了!你知道吗?”秦瑾说:“知道了。”又停了一下,焦先生继续说:“其实我很理解老舍,士可杀不可辱,读书人凛然正气嘛!告诉你吧!我多少次想走老舍这条路,为了可怜这两个孩子,我从护城河边又走回来了。她们小小的年纪,读不了书,又当了狗崽子,任人欺凌,我什么也没有留给她们,要是再给她们背上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她们怎么活下去啊!所以我一直硬挺着,忍受着不堪忍受的凌辱。”秦瑾听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焦先生回忆说:“记得几年前在首都剧场开梅兰芳的追悼会,那天我紧排在老舍的后面,老舍回过头幽默而感伤地对我说——‘焦先生,在死神面前我们也正在排队呢!’这话深深地埋在我心里。”他提高声音说了下去,“我多少年有个习惯,每天晚间上床脱鞋时,总要默念着明天该完成哪几件事,可现在我每天晚间上床脱鞋时,心里默念着老舍,我说,老舍啊老舍,我是紧排在你后面的一个,带我走吧!明天别叫我再穿上这双鞋了!”说到这里,焦先生强忍着满眼的泪水,赶忙摘下近视眼镜拿在手中,反反复复地用手擦起来…… 焦先生曾经由于医院治好了,这时因为身心受尽折磨使视网膜再次脱落,但是再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他住在小黑屋里光线很差,又毫无办法,只能在桌子上放一块吸铁石,把一些钥匙、剪子、小刀等工具,都放在吸铁石上,以便于用着方便。而且,焦先生常常在内心痛苦难以控制的时候,跑到北京城墙根儿大哭一场。他曾经自言自语地说:“没有文化的人,搞文化大革命,把几千年文化传统都搞掉了,留下的是打、砸、抢文化。像老舍这样的人才,五十年、一百年也不一定能出一个,活活地硬给逼死了。这个损失比自然的灾害要大得多啊……” 就是在这样一种精神近于崩溃的情形下,焦先生感到胸部医院,并确诊为晚期肺癌,动手术也已经无济于事了。医生们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没有把这个不幸的“判决”告诉病人,但是焦先生还是通过病床栏杆上的卡片,从一般人并不认识的拉丁文字里,知道了是得了什么病和严重到了什么程度。 焦先生为了不给亲朋好友们带来痛苦,面对这一切装作什么也不了解,只是平静地要求见见下乡插队的大女儿焦世宏。当他见到从延安赶回来的焦世宏以后,出人意料的竟然说出这样一席话来:“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戏剧著作都多,可惜全是交待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我的来日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只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要把它留给后人。我自信自己还可以再活两年,你要把我说的都记录下来。我要争取把自己多年探索实践的收获,比较系统地整理出来交给后人。我现在是生命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什么顾虑也不会再有了……然而,这可就要为难你了,孩子!” 焦世宏还没有把父亲的话听完,就已经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了。她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只能连连点头表示要照此办理。 在这以后,焦世宏为此准备好一个像样的大笔记本和一支钢笔。 然而,事与愿违,焦先生由于对化学放疗的反应非常强烈,病情急转直下,很快就进入了弥留的状态。万分遗憾的是,在他就要离开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的时候,连自己最后一个善良的、崇高的愿望也没有能够得以实现。人们对此也只能是欲哭无泪,愤愤不平,又束手无策。 焦先生在病床上辗转反侧,疼痛难忍,唯一使其牵挂的事,是焦世宏按照政策规定早应办理却迟迟没有办成的回到北京之事。当焦先生在病床上紧紧拉着女儿的手,用含糊不清的话问:“你……的户口……落上……了吗?”焦世宏点头答:“您放心吧,已经落上了!”这时,焦先生才面带笑容地合上了双眼,撒手西去。 值得一提的是,当医院把病危通知书送来的时候,“军工宣队”的负责人赶到病房,竟然大声地追问:“焦菊隐,你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问题要向组织上交待吗?”当焦先生微微摇头以后,负责人立即向家属宣布了三条必须遵守的“规定”:1.不许给死者尸体穿衣服,只能用一条旧床单包裹起来火化;2.保留骨灰的木盒子只能使用最便宜的7元钱一个的;3.不许选墓地立石碑,骨灰盒也只能存放在八宝山公墓的地下室里。 焦菊隐先生——一位博学多能,才气纵横又著作等身、硕果累累,而且桃李成蹊的当代中国戏剧大师,于年8月28日,享年69岁,悄悄然地、冷清清地、有悔有怨有恨地走了。他永远不会回来了,永远不会再说出想说而又没有说出来的话了。
写作契机
夜里,久久不能入睡,后来勉强睡着时,我又梦到了一位高高的个子,消瘦的脸庞,两只高度近视而又忧郁迷离的眼睛,沉默愤懑的目光,根本不吭一声的老人,在直愣愣地、毫无表情地从凄风苦雨里走来,一动不动凝视着我……我的心要碎了,又连连摇头无言以对。 或许,这将成为我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人心中永远的痛。 此刻,我才忽然意识到焦菊隐先生已经离开人世间整整40年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艺建院半个世纪有余了。这座被誉为“国际艺术殿堂”的大剧院,在经历过60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道路以后,在演出了一大批经得起历史和观众考验的优秀剧目,造就了众多杰出的导演、表演艺术家,磨砺出了以民族化现实主义为主要创作方法的“北京人艺演剧学派”之今天,也许,最让我们深深怀念着的就是可敬、可爱的焦先生了。 焦先生早在年就受人之托,创办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大胆采用了新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毕业学生中有一大批著名京剧演员都是他的高足,例如傅德珠、宋德珠、李和曾、王和霖、王金璐、李金泉、李玉茹、侯玉兰、陈永玲、高玉倩,等等。年,焦先生到法国的巴黎大学攻读文科学士,后来写出的博士论文是《近日之中国戏剧》。年,焦先生毅然回国投入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就任江安国立剧专的话剧科主任,教授导演、表演、舞台美术和剧本宣读等课程。同时,在大后方和北平先后导演了话剧《一年间》、《明末遗恨》、《日出》、《原野》、《桃花扇》,以及《夜店》、《上海屋檐下》,等等。新中国成立,他参加创办北京人艺以后,“为了创造具有民族风格、民族气派的中国话剧”继续导演了《龙须沟》、《明朗的天》、《虎符》、《智取威虎山》、《三块钱国币》、《茶馆》、《蔡文姬》、《胆剑篇》、《武则天》、《关汉卿》等一系列经典剧目。难怪有人说:“至今人艺演出的剧目中,仍然还可以看到焦先生无所不在的灵魂。”
来源:北京青年报
焦菊隐(.12.11—.2.28)
补骨脂酊白癜风的治愈